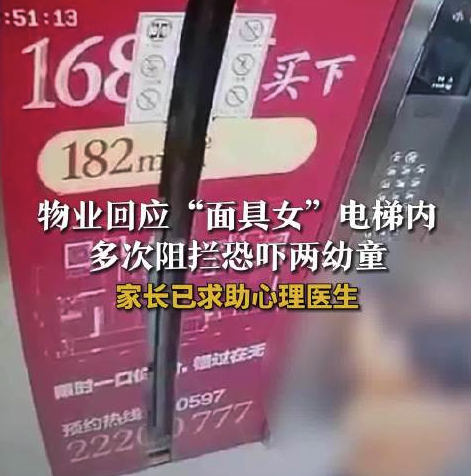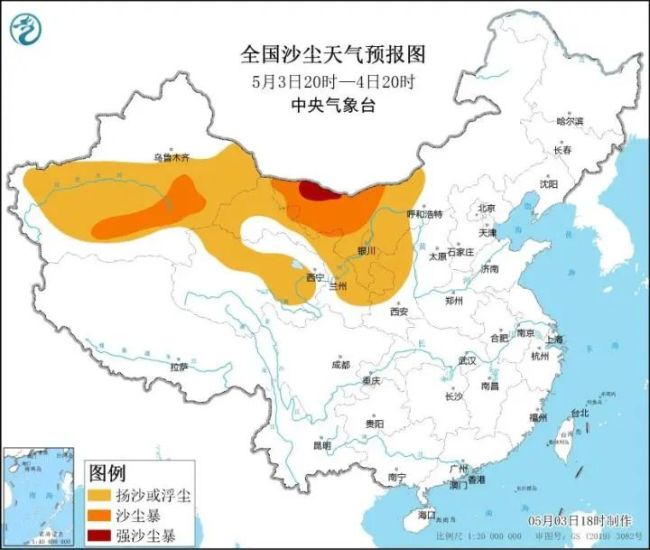女子起诉银行借1.12亿不还 一审重审
河北廊坊王萍起诉廊坊银行永兴路支行借款1.12亿元不还案,历经一审胜诉、二审发回重审,再次将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漏洞与司法裁判尺度问题推至舆论风口。这起案件表面是民事借贷纠纷,实则暴露出金融机构权力失控、司法证据审查困境以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系统性危机。
金融机构“内部人控制”的治理溃败
本案核心争议在于,时任行长杨娜以支行名义借款,却将资金转入案外人账户,且部分还款由第三方支付。廊坊银行在2017年已开除杨娜,承认其存在违规行为,但未能解释为何长达三年间未发现巨额资金异常流动。根据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》,银行需建立“岗位制衡、授权审批”机制,而永兴路支行公章管理、账户监控、行长权限等环节集体失守,暴露出中小银行“重业绩轻风控”的顽疾。类似案例中,某银行郑州纬二路支行客户经理席薇诈骗1.6亿元,其中6000万元用于直播打赏,该支行同样因“决议解散”注销——金融机构通过注销分支机构逃避责任,已成为行业潜规则。
司法裁判的“证据迷宫”与程序正义之困
一审法院以《借款协议》、微信记录、交易习惯等证据认定借贷关系成立,而二审法院则以“未签订书面合同”“资金未进入支行账户”为由撤销判决。这种“同案不同判”的矛盾,折射出司法对金融机构特殊性的认知分歧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469条,书面合同并非唯一形式,交易习惯可补强合意;但《商业银行法》第35条明确要求“银行与客户业务往来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”。本案中,王萍基于对银行公章和行长身份的信赖出借款项,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,而二审法院机械适用“合同相对性”,忽视了金融交易的特殊性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廊坊银行在诉讼中未提交关键证据(如杨娜授权文件、账户监控记录),司法机关也未依职权调取,暴露出金融案件中“举证责任倒置”原则的缺失。
金融消费者“弱者地位”与制度性救济缺失
王萍作为个人投资者,与银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地位失衡。其出借资金达1.12亿元,却未要求资金进入银行对公账户,反映出普通民众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信任。而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对“内部人犯罪”的追责机制存在漏洞:杨娜已被开除,但银行是否需承担管理责任?根据《九民纪要》第72条,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,单位未尽到管理职责的,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然而,实践中银行常以“个人行为”“已尽形式审查义务”为由推脱责任,导致受害者维权成本高昂。本案中,王萍需自行承担证明“银行存在过错”的举证责任,而银行却无需自证清白,这种制度设计加剧了金融消费领域的不公平。
破局之道:从“个案正义”到“系统治理”
解决此类问题需构建“预防-追责-救济”全链条机制:其一,强化金融机构内部治理,推行“关键岗位轮岗制”“公章电子化管控”等技术手段,压缩内部人操作空间;其二,完善司法裁判规则,明确金融机构表见代理的认定标准,建立“举证责任倒置”制度,要求银行自证无过错;其三,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,设立专门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,引入“惩罚性赔偿”制度,提高银行违规成本。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金融案件中,消费者胜诉率仅37%,而涉及银行内部人犯罪的案件,消费者获赔比例不足15%——唯有通过制度重构,才能打破“银行输了官司,消费者赢了判决却拿不到钱”的怪圈。
当1.12亿元借款纠纷演变为一场司法与金融的双重拷问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王萍个人的维权困境,更是整个金融体系治理能力的试金石。金融机构的公信力,不应建立在消费者的“盲目信任”之上,而应植根于严格的内部管控与公正的司法救济。毕竟,金融的本质是信用,而信用的基石,是每一个个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平等守护。